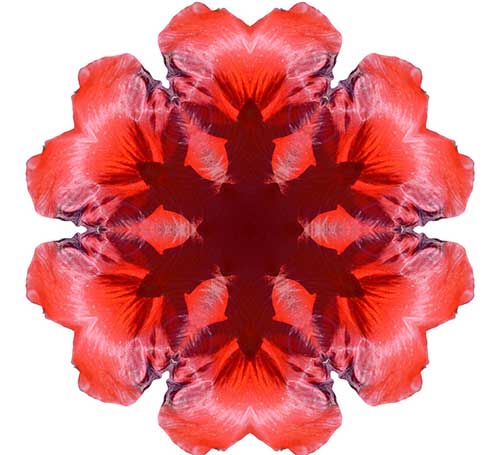印光——净土宗师 常惭愧僧
发布时间:2019-10-01 09:15:52作者:大悲咒入门网
印光——净土宗师 常惭愧僧 生老病死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思索人生根本与究竟的人都始终不能摆脱它对自己灵魂的缠绕。于是许多执着于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者,藉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某一宗教人生的存在。在灵魂无助之时,为它寻求一个依托来自救,以使人们在对幻化无常的人生感喟中立足脚跟。现代高僧印光大师的出家正是基于自己在病榻上辗转数载而对人生究竟发出的颖悟,从此“觉今是而昨非”,回心向佛。 印光大师,法名圣量,陕西郃阳县赵陈村人,名绍伊,字子任。法师弟兄三个,他排行最小。小时候随长兄读儒书,颖悟非常,曾考中秀才。15岁那年,在床上一病不起,如此有好几年。于是,在1881年21岁时,于陕西终南山五台莲花洞寺,从道纯和尚出家。第二年,又在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法师以净土为归,受戒前,曾在湖北竹溪莲华寺充照客,晒经书时,